1907年3月的第一个周末,荣格偕妻子与年轻的路德维希·宾斯万格一起来到了维也纳。多年之后,已是老者的荣格,将弗洛伊德称为“我所遇到的第一个真正重要的人”,他更愿意将自己第一次见到弗洛伊德的情形看作是自己开始聆听并向长者学习的一个重要时刻。人到老年之后对自己的慈悲确实可以歪曲记忆。事实上,在这次谈话中,荣格说得比弗洛伊德多多了,至少在谈话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如此。欧内斯特·琼斯有幸在1907年7月见到了荣格,他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关于第一次拜访,荣格跟我说了很多,说得很生动。他有很多想要告诉并询问弗洛伊德的问题,并且非常起劲地一直诉说了整整三个小时。然后,那个耐心且全神贯注的听者打断了他,并提出了使他们的谈话更为系统化的建议。让荣格震惊的是,弗洛伊德开始将其热烈的讨论内容归纳为一些明确的标题,以确保他们之后能够进行更多更有益的交谈。
……关于第一次拜访,荣格跟我说了很多,说得很生动。他有很多想要告诉并询问弗洛伊德的问题,并且非常起劲地一直诉说了整整三个小时。然后,那个耐心且全神贯注的听者打断了他,并提出了使他们的谈话更为系统化的建议。让荣格震惊的是,弗洛伊德开始将其热烈的讨论内容归纳为一些明确的标题,以确保他们之后能够进行更多更有益的交谈。
3月3日这个周日的夜晚,两人继续以这种方式一直交谈到凌晨两点才停止,历时整整十三个小时。弗洛伊德后来告诉琼斯,荣格是他所见过的最精通神经症的人。荣格对他也几乎怀着同样的敬畏:
……我到那时为止所见过的人里面,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他相提并论。从他的态度中您看不到任何浅薄轻浮的痕迹。我发现他极其聪明、敏锐和出众,而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依然有些复杂;我不能理解他。
他关于性的理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他的言论并不能消除我的疑虑和怀疑。有时我会试着提出我的异议,但每次他都会认为这是我缺少经验的缘故。弗洛伊德是正确的,在那些日子里我没有足够的经验来证明我的质疑。但我知道,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哲学角度,他的性理论对他自己都是极其重要的。
周一,荣格再次回访,这次宾斯万格就在他旁边。弗洛伊德询问他俩昨天晚上做了什么梦。他认为荣格的梦中有要“罢黜并取代他(弗洛伊德)”的愿望,而在宾斯万格的梦里,弗洛伊德觉察出宾斯万格想要娶他(弗洛伊德)的大女儿。气氛很好,弗洛伊德教授先生无声的威严展示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宾斯万格回忆道:
自我们拜访的第一天开始,从这些(梦)的释义中就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这种随和友好的气氛。弗洛伊德不喜欢拘泥于形式,他的个人魅力、坦率、自然开放、和善,至少他的幽默都是不受限制的。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他所散发出来的伟大与高尚的特质。尽管我有某种程度的怀疑,但也很荣幸能够看到弗洛伊德对荣格的回应充满了热情与自信,他几乎将荣格看作是他科学上的“儿子与继承人”。
弗洛伊德邀请他的两位客人参加3月6日的星期三心理研讨小组。这次由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来呈报案例。阿德勒报告的案例是一个俄国大学生,最后证明其有肛欲的趋势,这绝不仅仅是一次偶然。阿德勒和弗洛伊德似乎事先已经研究过这个案例。阿德勒报告说,在该病人的童年记忆中,他对自已阴茎的大小非常敏感,根据这一点,阿德勒将其作为引起神经症的原因纳入了自己的器官自卑理论之中。之后,阿德勒将病人的强迫观念与三个数字联系起来:3,7和49。最后,他讨论了病人的“犹太人情结”。在讨论中,弗洛伊德如此阐述了病人的强迫症:“3可能代表了基督教徒的阴茎;7,49分别代表犹太教徒的小阴茎和大阴茎。”之后,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弗洛伊德又继续讨论了病人的吝啬。阿德勒肯定了弗洛伊德对男性节俭品质的猜测,并提供了病人童年时期失禁的有关资料。这为弗洛伊德得出最后结论提供了良机,以下是兰克的会议记录:
弗洛伊德教授指出,吝啬和过度浪费与肛门区的紧张有关。这些人在日后的生活中有着区别于人的特殊的人格特征:他们整洁、于净、有责任感、固执,并有奇怪的金钱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名患者症状的内容带有某种妥协的性质:就像这名患者在说,“我希望接受洗礼——但犹太人的阴茎依然相对大一点(因此我仍然是一个犹太人)”。
这涉及到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在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之间还有些细微的不同:在这个天主教城市里,像许多别的犹太人一样,阿德勒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策,选择接受洗礼,而弗洛伊德却没有这么做。对荣格来说,这是一个俄国学生的案例,而这个学生只是碰巧具有肛欲的特点。对其他成员而言,这个案例所讲的是一个在乎犹太人是否有大阴茎的懦夫。(几乎没人注意到荣格和宾斯万格是首次出席会议的非犹太人。)
可能是谨记着艾廷根的遭遇,荣格和宾斯万格整晚都保持着低调的态度。宾斯万格只问了一个问题,荣格也只是略微谈及联想实验中被试对数字的反应,并认为应当跟随弗洛伊德来赞扬阿德勒的器官自卑理论,但是他又请求弗洛伊德原谅自己,因为他承认自己仍在试图攀登弗洛伊德理论的巅峰。正如马克斯·格拉夫后来所回忆的,每个人都知道弗洛伊德欣赏这两位瑞士的访客,尤其是荣格。这种情感是相互的。荣格甚至在晚年的时候还很喜欢说弗洛伊德是如何之“英俊”。
这种情感并未扩大到弗洛伊德的团体中。据说几个月后,荣格告诉欧内斯特·琼斯说,很“可惜”,弗洛伊德的追随者没有任何影响力,他周围挤满了“堕落和放荡不羁的人”。荣格和维也纳团体的对立是因为——这大部分都是琼斯造成的——有人盲目地认为荣格有明确的反犹倾向,这是极不公正的。事实绝不是如此。在他第一次来访的时候,他依旧被自己浪漫的犹太情结(这是最好的一个解释)所支配着。他被极具犹太人性质的精神分析吸引,也正是因为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他被犹太女性所深深地吸引着。如果犹太教的知识分子们在19世纪传统的欧洲文化占据主流之前就开始行动,荣格定会加入他们,尽管可能是从另一个方向加入。因为很早就已经放弃了自幼被灌输的瑞士加尔文主义,荣格没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教会;对他来说,犹太教和神秘主义一样,就是建在隔壁的一座迷人的教堂。荣格试图从这个让他父亲无比失望的宗教中解放出来,他想要通过这个行为与集会中的那些人成为朋友,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事实上,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施皮尔赖因明确地描述了荣格对犹太教的态度,她说他“努力通过一个新的种族来探索其他的可能性,努力将自己从父亲的指令中解放出来”。
可以肯定的是,荣格的观点后来发生了改变,而且他也愿意认可自己的反犹主义立场。但是这种堕落的转变还远在多年之后,而那些导致这种转变发生的事件,其时也尚未发生。这并不是荣格不喜欢弗洛伊德周围那些维也纳人的原因。需要郑重声明的是,荣格从未提及弗洛伊德的团体是犹太教性质的,尽管他毫不遮掩自己对他们的厌恶。那时琼斯也不喜欢这些人,却很愿意讨论他们的犹太主义。关于阿德勒,琼斯写道,他“很阴郁,并渴望得到情感上的认可”。对伊西多尔·萨德格尔的描述则是,他“是一个孤僻、可悲的人物,非常像一头笨拙的狗熊”。希奇曼得到的评价只是“不露感情、机智并有些悲观”。“臭名昭著的斯特科”最终得到了特殊的对待。至于这个团队整体,琼斯写道:
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个集会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是,在维也纳的那些日子里,弗洛伊德的天才招致了无数的偏见,很难担保一个学生的名誉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因此,他不得不接受他身边的这些人。
这么说来,弗洛伊德确实并不怎么关心这些人。在3月6日的星期三研讨会上,用宾斯万格的话来说,弗洛伊德“把我带到一边,然后说,'好啦,现在您已经见到这帮家伙了’”。宾斯万格对这句评论的反应,就是使自已明白了一点:尽管弗洛伊德相对孤立,但他的社交判断能力依然十分“犀利”。
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产生的这种关系具有一种特别的性质,很多人曾经描写过这一点。这种情感就像爱一般。你可以说弗洛伊德需要一个理想的儿子,而荣格需要一个理想的父亲,当然了,他们只是在扮演这些角色。换句话说,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是不匹配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秉性以及在各自的雄心壮志中被赋予的不同而特别的角色。另外,当时人们甚至还不能弄清他俩之中谁更重要一些。弗洛伊德资格较老,但是过去的两年间,荣格在国际学术界声名鹊起,令人印象深刻,几乎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
更为重要的是,荣格的工作并未引起争论。事实上,这两个人正在进入同一个研究领域(对无意识心理过程的阐述),而他们却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出发,如果要求当时的时事评论者从中选择一个尚能接受的观点,那么他一定会选择荣格的观点。这不仅仅是因为荣格关于情结的理论饱含着情感,它远不及弗洛伊德提出的多相变态的力比多理论那么令人疑窦丛生,还因为荣格的理论已经在实证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弗洛伊德依然有着绝对不容忽视的优势:无与伦比的德语表达天赋,大量原创性的观察研究,令人望而生畏的系统性以及对自己理论正确性持有的坚定而无声的信仰,这还只是随便说说,就已经有四个优势了。但是,面对这位热情洋溢的访客,面对这个苏黎世精神病学会主席显而易见的继承人,弗洛伊德的处境就像是一个大学里面的助理教授正在迎接阔绰的亲戚忽然光临寒舍——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冷静就是最大的技巧,将精力集中于谈话之上,而且要看起来什么也不缺。况且,弗洛伊德也不清楚荣格到底有什么打算。弗洛伊德解析了荣格的梦,这个梦泄露出荣格想要取代他的愿望,其实弗洛伊德这次毫无敌意的解析已经接近了当时真实状况的内核:荣格已经立志成为一个先锋性的深度心理学家,而且从专业角度来看,他在未来几乎可以任由自己的喜好来发展。简而言之,对双方来说,有着足够的余地可供他们谨慎地行事,让他们持怀疑论调,彼此揣着不信任感。双方已经有了直接的接触,弗洛伊德几乎可以说是毫不遮掩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而荣格也感到自己最终获得了一位伟人的赏识,对这两位来说,上述的那些怀疑和不信任感似平都已消失了他们的这次相聚,各自早已在私底下进行过认真的排演,而且谁都不愿意让这一刻留存为失望的瞬间。双方都终于找到了一位值得去了解的人,这种幸福使得彼此之间的理解变得容易多了,他们成为知音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本文来源于正道心理正道心理-https://www.psyzd.com/10685.html 本文来源于正道心理正道心理-https://www.psyzd.com/10685.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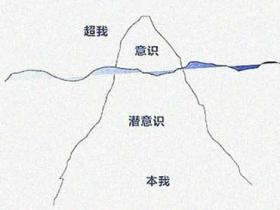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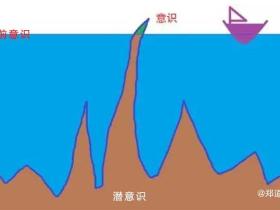

辽宁省大连市 1F
弗洛伊德是牛人